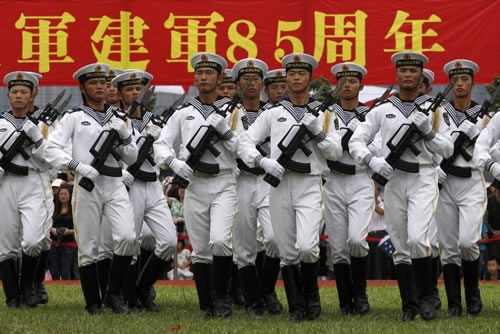1966年1月,我从黑龙江七台河市桃山矿子弟小学教师岗位上,应征入伍(兵龄按三月份计算)。到今年3月虽然半个世纪过去了,但那段往事,仿佛就在昨天。下面我想讲讲当兵那些事,与各位战友分享。
我所在的连队,是沈阳军区炮兵第62师605团一营4管高射机枪一连。在当战士的三年中,很巧合地实践我军的三大传统职能,即生产队、战斗队、宣传队,当上了生产兵、战斗兵、宣传兵,使我受到了很大的锻炼,以致终生难忘。
(一)“生产兵”。刚入伍时,新兵连的营地在丹东市原八一小学。为了尽快克服摆脱社会青年个体生活的自由散漫习惯,新兵是早出操、晚点名、整天喊着“一、二、三、四”口号,苦练齐步、跑步、正步走和各种队形,培养良好的军姿、军容、军纪。每周还加训投弹和射击,有时在训练场上一趴就是半天。好在我原来在学校有体育锻炼的基础还吃得消,有的体能差的兵一天训练下来,爹一声娘一声的直叫。
一天中午,刚端起饭碗,就听到外面老百姓大喊“失火了!”。连长马上集合全连奔赴火场。只见丹东市颜料仓库,烟雾里夹着烈火贪婪地吞噬着库房。在连长指挥下,我们操起水桶、扫帚等工具,同工人们奋力扑救,为了减少国家财产的损失,不顾烟熏火燎,大家冲进库房抢运成品颜料和各种生产物资。经过两个多小时的奋战,大火被扑灭了。再看看我们个个是大花脸,浑身都是五颜六色,集合时根本辨不清谁是张三李四。返回营房时,引来了不少的围观群众。回来后拿起肥皂就往鸭绿江边跑去,洗脸、洗衣服。衣服上的颜色很难洗掉,就用沙泥往下搓。本是草绿色的军装,都变成了灰色。新兵两个月的训练很快结束了。我在队列、投弹、射击的考核中,均取得优秀成绩。有一天下午,有人告诉我说“连部有你的电话”。头一次进连部,看到连里领导心里有些紧张,加之从没有摸过电话,拿起来就喊,啥也听不着。周围人边乐边说“你把电话拿反了”。弄得我十分尴尬。电话拿正后,才听到对面老乡说,他们已下到班里开始操炮了。我心想,我们这边连枪都没看到。后来听说,连长还在郑州炮校集训呢,是为了增强低空火力,新编配了高射机枪连。过了几天,团里给我们下达了任务:主业是种水稻,补给全团细粮不足,副业是采石,为团里搞营建备料。三月末,我们全连开赴离丹东市几十公里的采石场,住进东沟县黄土坎乡黄旗村老百姓家里。我们手中的武器就是大锤、钢钎、抬筐、木杠。我每天除抡大锤、打钎子,还担负着点火放炮的任务。爆破下来的石块,有的重达二、三百斤。有些爱挑事的人说“李老师抬一块”。由于年轻好胜,我还真不服,谁跟我叫号,我就跟谁抬,有时杠子一连压断好几根。初春,我们又转战大孤山脚下小甸子农场,开始做种水稻的准备。每天要徒步往返四十里路,扛着铁锹等工具,从驻地去农场,平整土地、挖水渠、灌水。我从小就有遇冷风冷水过敏的毛病,挽起棉裤腿下到刺骨的冰水里,两条腿很快就红肿起来,硬得像棒子一样,收工时仍坚持步行回到驻地。那天晚上,有一个民房起火。火光就是命令,我不顾双腿麻木和沉重,和战友们一起奋力救火,事后受到连里的嘉奖。当时,正是青黄不接的季节,每天三角九的伙食费,吃的菜都是老连队送来的糠萝卜、干白菜,高粱米饭粒硬的,掉在盆里都能砸出响儿来。开始老百姓都认为部队吃的是大米白面,后来发现连队的战士们天天竟吃这些,有的房东就给我们送点儿大酱、咸菜或几棵大葱。从三月到十月,我们往返于石场和稻田,一天训练也没搞。有的战士风趣的说:“知道这样还不如让我爹来啦。”我由于自己辞去了每月30多元工资的老师工作,到部队领六元钱服兵役,还能在政治学习带头发言,写读书笔记。生产劳动中吃苦耐劳,经常到炊事班帮厨。业余时间教大家唱歌,自编自演一些小节目参加团里汇演。入伍半年多,就被团里树为先进典型,还光荣出席全师召开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。十月份,经过平地、浇水、插秧、施肥、除草等环节,金灿灿的稻子成熟了。开始收割脱粒,就是在脱粒时,我发生了意外事故。那天早上刚上工,我正在机前收拾刚刚脱出稻粒。班长看到稻捆有些积压,让我到机后帮着打捆。我由于着急就跳上板凳,想从动力传送带跨过去,左脚不慎碰到传送带上,人瞬间被卷进皮带轮里,昏了过去。后来听说作为动力的东方红拖拉机马达被憋灭火了。机工赶紧将皮带拽下来,将轮轴拆卸开,把轮盘和人一起抬下来。我的左腿和穿的外裤、秋裤死死地扭在轮轴里。卫生员用剪刀把裤管一层层、一条条的剪开,然后,顺轴心一点一点地往外绕,经过一个多小时,才把人和机器分开。庆幸的是大腿骨没断,只是大腿里的皮肉绽开,一片血肉模糊。简单进行包扎处理后,被送到丹东230医院。在治疗期间,师宣传科报道员、原同连老乡来看我。他说:“你快点把腿治好,部队很快就要出国参加援越抗美战斗。”我当时想,已经是死过一次的人了,还怕什么,当兵不打一次仗,不上一次战场,就白穿一次军装。我再也躺不住了,就一瘸一拐地找到了护士长要求出院。护士长说,你大腿的溃疡面很深,你怎么走。我一看说不通,又去找医生磨,医生看我的态度很坚决。就说,你再住三天,好好地给创面清理一下,多换几次药再出院。病友也都劝我多呆几天。三天后出院时,全科的医生、护士、病友都出来送我。这时,我们连已随全团在丹东市集结待命。为了方便卫生员换药,我暂时住连部里。我们编配的高射机枪还没到,无法训练。每天主要是进行爱国主义、革命英雄主义和忆苦思甜教育,激发参战的热情和斗志,全面做好思想、精神方面的准备。出发前几天,我回到班里参加训练。11月中旬,全师接到军委命令,向广西边境集结。我们乘了一周的铁皮闷罐车,到达广西崇左县临时驻地,开始近两个月的战前训练。
(二)“战斗兵”。我所在的九班,班长胃出血住进南宁部队医院治疗。部队出发前,连里指定副班长代理班长,我代理副班长。1967年1月26日,全体指战员都换上越南人民军的服装,戴上盔式帽,集合在友谊关前,向党、毛主席和祖国人民宣誓:誓死保卫祖国、为“五大争光”,为越南人民报仇,坚决将美国佬赶出越南。部队开始陆续向越南进发,我连还没走出多远,在一个桥头弯道处,三班的牵引车翻到三米多深的沟里,车上的人、弹药、粮食等全扣到车下。看到前面的车都停下来了,我让班里同志在车上不要动,我先去看看。当我看到扣在沟里的车,腿都软了。连长大声喊,九班副快叫后面的人拿大绳拽车,我紧张的上气不接下气的往后跑,传达连长的命令。各班人员纷纷跳下车,拿着绳子、锹镐等工具,跑到事故现场。先用大绳把车拉起来,再用砍刀、斧子,把大厢板砍开,随后把车上人和物资抬出来。当看到四位战友有的满脸是血,有的毫无声息软绵绵躺在地上,很多同志都哭了。特别是司机疯了似的,一边嚎叫,一边打自己脸,有几个同志过去赶忙把他拉住,不断地在劝慰和安抚。很快团里的卫生车和工程车都赶到,把人和车都拉走了。指导员集合全连对行军安全又进一步提出了一些要求,部队又出发了。地处亚热带,山高林密,车在崇山峻岭的“胡志明小道”上爬行。险峰峭壁下云雾缭绕。途中没有了开始的兴奋劲儿,还沉浸在事故的阴影里,心里还在惦记着生死未卜的几位战友。1月29日的凌晨,我们占领了越南北太省太原市发电厂附近一个山头阵地。把四管高射机枪下架后固定好,呈战斗状态,就开始挖掩体,构筑工事。因昼夜行军,人困马乏,进度不是很快,到中午吃饭时,掩体才没小腿那么深,帐篷也没搭起来。午饭后,大家都在阵地边上的草丛里休息,下午2时左右,闷雷声般的敌机爆音在上空响起,随着警报的鸣叫,战斗人员都迅速进入各自的岗位,勤务人员依旧坐在坡下的草草丛里。美国14架“F105”飞机十分猖狂,低空进入我防区,对越南人民军阵地、发电厂等建筑物进行狂轰滥炸。我们坚决执行“集火近战”的原则,待敌机靠近时,全团一起开火。霎时,火光冲天,天空像开了锅似的。特别是我们的四管高射机枪连,一分钟可以打出600发子弹,射击时像礼花一样,把敌机团团围住,阵地上硝烟弥漫,尘雾滚滚,战斗持续40多分钟,击落一架,击伤两架,取得了首战告捷。为此,我连也付出沉痛的代价,五班长光荣牺牲了,两名战士受伤。五班长也是全师部队援越抗美的首位烈士,师里为其追记二等功,并发出向他学习的号召。
我们吃的用的都由国内提供,连修工事的木板都是从国内带来的。坚决执行“三大纪律八项注意”,不拿越南人民一针一线。可谓是文明之师。越南人民对我们很友好。战斗间隙,阵地附近的老百姓,主动为我们送伪装草和树枝,送茶水。在转移阵地时,他们还冒雨帮我们往山上拉枪和车辆。我们每天吃的都是干菜或罐装咸菜,主食是线米。线米煮出来的饭,像白沙粒一样,又硬又散,不喝些汤或水,很难咽下去。最难适应还是越南的天气,可苦了我们这些北方兵。白天气温高达40多度,每天都是汗流浃背,睡觉的凉席会出现人体样的湿痕。汗浸的衣服得不到换洗,又洗不上澡,每个人身上很快长满痱子,一片一片的像赖蛤蟆皮,又痒又痛。我还因水土不服,经常拉肚子,浑身乏力,照样坚持修筑工事,参加战斗。越南的蚂蝗不但水里有,草丛、树枝上都有,经常掉进脖子里和爬到腿上。一天,我站哨回来,脱下袜就看到小腿一道血流,把裤管挽起来一看,两只蚂蝗叮在腿上。经验告诉我们,这时不能马上往外拽,这样会把吸盘留在肉里,造成感染。只能用鞋底子拍打,使其自动退出。
1967年4月份,我在火线上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。5月份,我被连里任命为五班长,接过烈士曾举过的令旗,带领全班出色完成各项战斗任务,全班荣记三等功。时任的师政治部主任带领机关的同志,来我连阵地慰问时,还为我班和我个人拍了战地照。时任团参谋长还深入我们班蹲点,了解战士们的战斗和生活情况,给了我们极大的鼓舞。全班决心打好每一仗,为祖国为人民再立新功。在我们赴越前,有批广西籍的北京高校的红卫兵和当地10名女红卫兵,在周总理的批准下,随部队出国参战锻炼,女生都留在师宣传队,男生坚决要求下部队参加实战。北京政法大学的一位红卫兵,分到我们五班。我和班里的同志都主动地帮助和照顾他,使他很快适应战斗生活。在我们班里生活两个多月,师里考虑他们的安全问题,在7月份把他们送回国内(十位女生继续留了下来。)八个多月战斗,全师共击落敌机100多架,牺牲80多位战友。临回国前,师首长和全体指战员都到烈士陵园,看望烈士,与烈士告别,看到同乡战友,同班战友,长眠于异国他乡,心里十分难受。我暗下决心,一定把兵当好,继承他们的遗志,出色地完成保卫祖国的任务。
对于生活在和平年代的普通人,是否敢于接受战争的洗礼,能否坦然面对生死的考验,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,有的畏缩不前,有的临阵脱逃,有的借故规避。我连集结待命时,从16军补入十几个兵员。其中有三个安徽籍的战士,来后就泡病号,后来发展到绝食,部队出发前将他们开除军籍,遣送回家由地方管制。我的原班长在南宁治好病,不告而别,跑回丹东部队留守处,后被开除党籍、军籍。还有炮连的一个战士被死吓破了胆,临阵逃跑,被抓回来后送上军事法庭判了刑。走入战争,都会有与死神擦肩而过的经历。我也是同样,五班长牺牲的地方,离我只几米远,距离死神只有一步之遥;一次,美机投下的气浪弹,只离我们阵地几十米远,空中飞落下来的弹片,像下雨一样发出沙沙的响声,落在身上不是死就是伤。大家高喊毛主席语录,坚守在枪位(越南人管我们这叫念经)。连队电话线被炸断了,上级指挥所看我连阵地被烟尘、气浪、火光笼罩,电话又联系不上,以为全连被报销了呢。还有一次,我带一个战士去砍树枝作伪装,发现树下有很多美机投下的子母弹(菠萝弹)。由于无知,我俩拣起来投弹比远,回来时我还带了两枚放在帐篷旁。晚上看《战地快报》时,才知道这些子母弹很多是定时的,炸死炸伤很多越南人民。我冲出帐篷,把两枚子母弹扔进很远的山沟里。特别是我代表全连去团里声讨美国飞行员时,得知六连一次战斗牺牲了十几位战友,还包括一位宣传股长,心里也有些打鼓。从集结待命至现在,有半年多没给家写信了。夜里我给家里写了两行家书:“请爸爸妈妈多保重,我这里一切都好,切勿挂念和惦记。”为保密所有寄出的信件不能封口,要经连里检查后才能发出。这实际带有诀别的意思。没收到家里的回信,却收到一封我高中同学的一封信,讲述国内文化大革命的情况,并说某个同学被打了,某个老师被斗了。我看了很气愤,“有劲上这来使,自己人打个什么劲儿”。参战几个月,心路走向大体是,开始不知道怕,毕竟在和平环境长大,参战主要是为了锻炼,又是高炮部队,不像步兵那样面对面的刺刀见红;随着仗越打越大,看到有那么多的战友牺牲在战场上,心想既来之则安之,该怎么样就怎么样,豁出去了;在得知部队要回国的消息后,有些厌战情绪,每天起来都希望今天最好没有警报声。人性弱点都差不多,有意志、有信念、肯坚持,就能过好人生的每一道坎。8月25日,全师部队从水口关回国,一路欢歌笑语。在小憩时,我们高兴的把车、枪上的伪装网和树枝全部撤下来。坐在敞篷车里,尽情地呼吸祖国的空气,眼睛都不舍得眨一下,看着家园的山山水水。此时,国内红卫兵运动如火如荼。即使是出国作战部队,他们也不放过围堵和检查。列车在柳州停了大半天,据说造反派互相开枪打派仗。根据团里的要求,我们把轻武器都拆开,把枪栓和弹药都藏在米袋子里。就这样造反派还把团里的指挥车抢走,还抢走了不少军装。我们特别不理解,我们在国外流血牺牲作战,回国却遭遇这种“待遇”。全体指战员还是坚决执行上级有关“打不还手,骂不还口”的指示。9月3日,我们终于回到阔别九个月的丹东市,我连住进东尖山的兄弟部队营房,恢复正规训练的生活。
(三)“宣传兵”。为了参加全师表彰大会的调演,团里下令调我去团里宣传队。到团里一边编节目,一边参加排练,共排练十五六个节目,经过团领导审定,最后精选了十个,时间一小时左右。11月中旬,师里召开“四好连队五好战士”总结表彰大会。我团宣传队被安排大礼堂晚场演出,师首长和全体与会代表都来观看。我自编自演的一个大批判节目,由于演得卖力气,也很出彩,得到师政治部主任和师宣传队长的赞扬。演出结束后,回到连队第三天,收到师部的调令,让我马上去师宣传队报道。临走那天早上,连长、指导员让厨房做点特殊饭菜,为我送行。可我一口也吃不下,就像一个要离开家、离开亲人的孩子,一个劲地哭,要求留在连队。连长和指导员让我闹得也没吃什么,轮番做我工作,又安慰又劝导:作为军人就要执行命令,出去要当好连队的代表,要为连队争光。上车时,很多同志都赶来送别。就这样我依依不舍地的离开了连队,离开了朝夕相处并肩战斗的战友。
来到师宣传队后,自己与多数专业演员还是有很大的差距的。只能是跑跑龙套,有时报节目,有时串个场。后来,队里为了培养锻炼我,为我量身创作独幕话剧《战斗英雄王克京》,演出几场反映还可以。为宣传弘扬援越抗美的英雄事迹,先后到几个地炮师巡演,受到好评。为配合地方“文革”中各派大联合,除了在本部队演出,我还和全队同志,包括前边说到的那10位女红卫兵(已正式入伍),还随师里的宣传车,深入到厂矿、学校、街道演出。四月份,队里为了进一步发挥我的特长,派我到师新闻报道培训班学习,提高编创能力,回队重点从事编剧工作。
六月份,培训班结束了。根据我的自身条件,不想回宣传队,就找到时任宣传科大批判组负责人,要求留在报道组。他说,“你是想留在报道组,还是回宣传队,确定后我可以去做工作”。我当即表态要留下来。经他与主任汇报,又与宣传队长进行沟通,我顺利地留在宣传科报道组。生活上发生很大变化:住单人床,吃食堂,有澡堂,每天喝的开水都有人送来。与基层连队相比可真是天堂了。所谓的报道员,就是文字记者。经常随领导下部队搞调研,发现挖掘新闻线索,回来后一方面撰稿成内部材料,还可改写成新闻题材对外宣传报道。为了稳定地方,全师抽出很多干部参加“三支两军”工作。一些干部在地方厂矿、机关、学校、社区、县乡(镇)任革委会主任。那些年,地方新闻报道系统基本瘫痪,我们还肩负地方的报道。因为我有一定的文化基础,进入角色比较快,在邮局、药厂、织袜厂、公社采写的一些稿件,很快见诸报端,增强做好这行的信心。在宣传落实毛主席最新指示时,坚持不过夜,有时一写就到清晨,然后赶紧乘火车到沈阳,把稿件直接送到“辽报”、“前进报”编辑的手里,如果编辑提出修改意见,连饭也顾不上吃,改好后再送去。为了写好一篇稿件,那真是绞尽脑汁,吃不好、睡不着,“爬格子”真是一件苦差事。五月底,当兵满三年,军贴由6元涨到10元。一天,报道组长找我谈话说,经过政治部领导同意,干部科已下令了,你被任命为605团宣传股新闻干事,行政级别23级,工资52元。我当时都惊呆了,做梦也没敢想,我能成为一名解放军的军官,第二天,扛起背包,坐上公共汽车,到东沟县黄土坎公社605团驻地报到。从此结束了战士的生活,步入军官的行列。
李成福
2016.3.1
附:4张当年照片
|